Pedro Brugada教授向《心髒病學管理》講述了塑造他心髒病學事業的公共和私人成就。我們還了解到他和他的兄弟們留下的科學遺產,作為第一個描述“布魯加達綜合征”的人,這是一種由心髒節律嚴重紊亂引起的心髒性猝死的遺傳疾病。
在心率管理中心,我沒有標準的、典型的工作日。
我們在電生理學實驗室的一天通常在上午8:30左右開始。我不斷地從一個緊張而迷人的活動轉向另一個。我首先會見了臨床電生理學項目主任Andrea Sarkozy博士和心房纖顫項目主任Gian Batista Chierchia博士。我們討論患者的特點和問題,並開始一個明確的診斷和潛在的治療方案的程序。在檢查了心律失常治療計劃並設定了當天的目標後,我和我的公關、行政協調員克裏斯蒂安·範·卡倫伯格(Kristien Van Caelenberg)以及我的妻子一起搬到了辦公室。在開始協商之前,我們會與承包商、支持者、官員和公司舉行會議。
kritien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獎學金計劃。我們有一個固定的小組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六名電生理學和起搏器研究員組成。一些人獨自搬遷,另一些人與大家庭一起搬遷。管理這些同事的不同需求並不容易,而Kristien作為“鴨媽媽”的角色意味著她經常在部門裏被一群不同的同事尾隨,這些同事依賴她的支持。
我們在電生理實驗室玩得很開心,玩我們的尖端設備:三個電生理刺激器,高科技記錄儀,三個用於電解剖重建和心髒測繪的三維測繪係統和磁導航。我們的外科醫生弗朗西斯·韋倫斯教授和他的團隊負責治療病人過程中出現的燒傷、凍傷和割傷。Carlo de Asmundi博士與護士長Marc de Zutter合作領導技術部。
調查每個患者不僅僅需要評估他們的醫療數據。
我的谘詢也是一樣的。我個人每年在心髒病門診接待2000到2500名病人,在亞伯拉罕·貝納塔爾教授的兒科節律中心接待另外數量不定的兒童。絕大多數病人是為了第三個、第四個甚至第10個意見而來的。他們在地圖、USB驅動器、cd和打印頁麵上保存了大量數據,上麵記錄了所有以前的訪問、在其他醫院的調查結果和從互聯網上收集的數據。
然而,我的第一項工作是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然後問病人:“告訴我,你為什麼來找我?以及“最初是什麼讓你去看醫生的?”許多病人的問題很簡單,但卻很容易解決。然而,我經常與診斷或懷疑患有布魯加達綜合征或其他遺傳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打交道。除了每天的電子郵件,來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們也來這裏尋求遺傳性疾病產生的數百個問題的答案。我們與遺傳科有著密切的合作,我們的研究護士斯特凡·亨肯斯(Stefan Henkens)負責為這個非常脆弱的群體協調所有必要的方麵,包括社會和心理方麵與我們的心理學家瑪麗娜(Marina)的合作。
除了周二,我和克裏斯蒂安每天晚上都是最後離開部門的,因為周二谘詢師們會在深夜進行谘詢。一旦離開醫院,其他計劃好的“驚喜”在等著我們:去日本開會的飛機,或者在當地與全科醫生的教學會議。從1月到6月,從9月到12月,會議通常每兩個周末舉行一次。社交時間不多,但我盡量擠出時間打高爾夫球,與朋友和家人相聚。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公共榮譽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但有一項私人榮譽超越了科學成就。
我在職業生涯中獲得的公共榮譽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名加泰羅尼亞人,我最大的榮譽是獲得加泰羅尼亞政府頒發的Josep Trueta醫學獎章,以及加泰羅尼亞心髒病學會頒發的金獎。就我個人而言,最打動我的演講是1999年我父親去世時,我在村子班約萊斯(Banyoles)的墓地做的一場演講。在他去世之前,我們有幸向他展示了第一本關於布魯加達綜合征的專著。我們把他和那本專著一起埋葬了。我的演講和當時非常有限的家庭觀眾的感受,留給你們想象吧。
Brugada綜合征的描述對我和我兄弟們的職業生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種綜合症對我和我的兄弟約瑟普和雷蒙的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知道,創造科學遺產是我們的幸運。我們還描述了短QT綜合征及其遺傳機製和一種家族型的預激。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說,布魯加達綜合征從一個隻有8名患者的科學奇案,變成了理解遺傳性心電活動障礙的參考點。沒有電,就沒有肌肉心髒收縮,因此,就沒有血液灌注,就沒有生命。
為了在心髒科獲得第一名,我不得不努力奮鬥。
在22歲完成我的醫學學業後,在加泰羅尼亞比利牛斯和塔拉戈納做了一年的全科醫生,我去巴塞羅那大學醫院診所的首席醫學主任,血液學家Cirilo Rozman教授那裏申請一份血液學培訓生的工作。他說我太年輕了,還得再等一年。
然而,我的第一個女兒伊莎貝爾即將到來,意味著這樣的等待是我無法承受的奢侈。帕科(弗朗西斯科)納瓦羅-洛佩斯剛剛成為新的心髒病科主任,他與阿馬迪奧·貝特魯和希內斯·桑茨合作,創建了西班牙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心髒病中心。因此,我提出了我的案例,作為一個在帕科的心髒科住院醫生的職位。與這三位傑出人物共事每天都讓人興奮不已。他們比其他人領先了好幾光年。從那以後,醫院的診所一直保持著這種現代化的聲譽。我哥哥約瑟和雷蒙還在那裏工作。
當我回顧我作為住院醫生的日子時,某些記憶很突出。
從1976年到1979年,我是心髒病科的住院醫師。在心髒科這段獨特的時光裏,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湧上心頭。作為一個居民,我的收入還算不錯,作為一個男人,我可以租一套小公寓,每天買一兩個三明治,開一輛舊摩托車。然而,作為一個有女兒的已婚男人,每一個比塞塔都很重要。帕科知道一個三明治對我來說太貴了,他發起了一種醫療遊戲,這樣我就可以“賺”到午餐。他真正的愛好是先天性心髒病。在星期四,我將和他一起為前超聲心動圖時代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兒童做心導管檢查。我們唯一的線索是臨床病史、體檢、心電圖和胸部x光片。然後他會給我看心電圖、x光片,並告訴我臨床病史和身體檢查結果。如果我做出了正確的診斷,他就會請我吃午飯。 I can tell you that no resident in cardiology ever learned so fast as I d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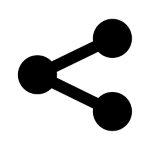 分享
分享



